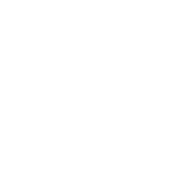攝影,幾乎成為現代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習慣。由於科技的YtZV80KuqbC0L=7rVzWlVmmZ@B4*By31zhGF$qSBNiQK!d8Em3普及,人手都能有一支像素1000萬以上的相機手機。而臉書與Instagram的流行,也讓人們更常以視覺來表現自己。
在主流男同志文化中,顏值、肌肉等自拍元素是用來推銷自己的利器。然而該怎麼呈現出不一樣的自己,把自我特色展現出來,關係到_^MvJg@kgvuzofENTB$DR_XPni@83R5g6(68)KH@exwlH!iTO9攝影究竟是怎樣的一門學問。也許我們可以從國際知名攝影師-沈瑋身上習得更多。
沈瑋出生並生長於上海,取得紐約知名的視覺藝術學院碩士SnU+wrs-DzZuQyiy4P&dVB(Zxai7r*2EMU*#yhtK-nre6Z=!=e,現居住於紐約。他的作品在各大知名攝影刊物與美術館展出,也受到MoMA現代美術館典藏。沈瑋的作品中有許多的自拍照,他認為自拍是自我回顧與探索的過程。同時也有許多人物的裸身圖像,探究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與性等命題。
嘎編第一眼看到沈瑋是在餐廳,我們與他共進午餐。沈瑋當時全身黑色,上身T恤,下身則是寬版的休閒褲,顯現出俐落的藝術家形象。午餐時沈瑋的聲音輕柔,帶著微&_qbXVS*RLNddPQmauvHOh=*AH)tN@mBSULT1&bCZKZS$Z1jv_微的中國口音,跟我們談紐約的變化,談藝術界的生態,談自己的經歷,而後談他自己的作品。

國際攝影師沈瑋
Q:能夠描述一下你的攝影過程嗎?
我會先架好相機,然後與模特兒到定點開始互動。譬如聊天,聊了兩小時,這兩小時可能沒有任何紀錄,但它是非常重要的過程。當我認為有個時刻很適合攝影,Pp6$jsGy6T4i3kGc&yACpwApq3zj$vrgkDz00g6GBOo&JykUYg我才會開始拍照。但是那時候一定要是我與模特兒處在非常自然的狀態,最起碼不會對相機的存在感到恐懼。這個過程可能長達幾小時。
我經常說作為一個肖像攝影師,你就是一個帶著相機的心理學家。可能LE6@wF^YY*(a^geV6YaYRyHIvZk4OOI8VtR%#V@=QlqGyigz*g拍照是一剎那,但是過程是非常深度的心理交流,譬如眼神或者身體接觸,都會影響彼此的心理狀態。
有一次我在紐約的一p*+(ji9dJYi#_EXBWXuPLAEBP*Zf2r5!o(o)N1RtRe%ORj4=9d個小城市當駐地藝術家。有一次我遇見一個非洲的留學生,我非常想跟他有一種關係或連繫。很難去描述這個感覺,可能是對他身分、身體或者更多可能性的好奇。我就邀請他來我的宿舍,我說「你就來,我們看能有什麼創作」。那個照片的過程是很自然的過程。雖然說有攝影這個環節,但是一旦相機架好,對好我們要的空間,我們之間的互動就非常自然。因為就只有我們兩個,跟一個相機,立刻就營造出來非常個人化、私密的感覺。我不用特別設計,這些照片都是很自然產生的。

沈瑋與非洲留學生的攝影作品
Self-portrait (Syracuse), 2010
(圖/Shen Wei-《I Miss You Already》)
Q:你有偏好什麼拍攝對象嗎?
當然我有自己的偏愛,但基本上我是一個處於開放狀態的人,不會刻意去尋找某種類型的人,男人也好女人也好。我之所以會想要拍攝9urhbUjbeog-$nkI36p-X$boup5zUEPoCq6s^p(pYG^Gza9j48,是因為我在旅程中對某些人或地點產生好奇,它們都偶然地反映我十年以上的攝影作品。所以在選擇拍攝對象上還是看感覺,透過互動,找到化學變化,它不一定要透過對話。
攝影就是很倚靠這種偶然性。我常常說我的作品是「feeVGt3m!)jPdEm%lI&AAGmxoq(Lb1#i5Bs%$TNE_kNL4!V(gAHdyling project」,我的每一個系列的起源都不是因為一個事件或主題,我不太為了一個概念去設計一個作品,而是一個本能,反映一個感受。我照片的意義或目的 ,通常很難直接地用語言去表達,這對我來說才會是真正由心裡出發的創作。

Self-portrait (Bamei), 2011
(圖/Shen Wei-《I Miss You Already》)
我從來沒有定義過我的作品屬於同志還是異性戀,因為我從來沒有定義過我自己。我覺得對藝術家而言,去創作或觀賞自己的作品最好的方式,是用最開放的方式。如果你(A1(J9U1nxYczzo&RCre3!=$hvYsBFtbH-OFGUIFlFG_ipmIb2一旦定義了,你就把自己放進一個盒子。我覺得定義是一個誤導,如果你定義了,你就在誤導你的群眾。同志與異性戀的定義,也是從觀眾去認定。
我對年老的人有很大i@ilx*TAt9#)lJ)@n)f6=Uybi&*y1K@+#Set#-n+jr4V=fT#d@的興趣,作品中有很多老人。因為他們跟我還是有距離,60隧到70歲、甚至80、90歲,我特別不熟悉他們的狀態,所以我對他們很感興趣。當代的年輕人都差不多,反而更難拍攝。而每個老年人有非常獨特的氣質。

Self-portrait (Touch), 2010
(圖/Shen Wei-《I Miss You Already》)
有一次我走到一個老人的花園,因為那時那地區很少有亞洲人,所以那個老人就過來問我為什麼到他的花園。一開始我還有點畏懼他,但接觸後我就沒那麼恐懼。他接著就邀請我進他家裡,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拍他的照片。而一旦我跟他進入一個私密的空間,之間的化學反應就有變化。那張照片拍了一下午,很多時間都在交談,彼此都在了解。這個過程是我沒想到的,一旦牴觸感消失了,進入私密空間rFDOd$fywKPSuk(GY!K+o&iP%4Az)=*LOV3jkZ%gc=S=_jDbX%,那個照片才能呈現它的樣子。

邀請沈瑋進房子的老人Arthur。
(圖/Shen Wei-《Almost Naked》)
Q:你有許多自拍作sX*oBhcBLdVbg+c4SkfHGuOYHGWVWJMzFJ%+ZiYra4hoUEooq7品,也創作了自拍攝影集《I Miss you Already》,請問它和其他自拍作品有什麼差異?
拍《I miss you already》時我已經自拍十年了,所以它在理念上與視覺上非常有系統。但是04年我拍過黑白的自拍系列,拍了一年時間,那時非常年輕,不太了解自己想做什麼藝術。《I miss you already》後的作品也會有自拍,但它們是為了連結作品。譬如《Between Blossom=T=J4MN)2041*ma7)PZ3xXFZBt8&kdqn7qDZu9bYx5hknYxTuf》這個系列,拍了些花、樹木、年齡,表現我對空間、植物、靈魂的理解,但是在作品間我用自拍串起來。這個作品是我在一個低沉的狀況下思考自己,視覺上光線都是很暗,包括自拍,就代表了我在那個時期的狀態。所以回顧自身作品,我就可以很明顯地知道當時的我在什麼狀態。

《Between Blossoms》的作品:Gallon Water, 2015
(圖/Shen Wei-《Between Blossoms》)
我覺得對著鏡子看自己,跟拍張照後再看,是非常不一樣的。因為你拉開距離,錯開時間、空間,看到自己在一個環境裡,在肉體層面來說,裡面的是另一個人,看到自己在一個環境裡。我經常覺得看自己的照片,好像在看另外一個人。在09年我還是處於摸索自己身體的狀態,看的都是非常直觀的東西,等摸索得差不多,就開始T-gpjh7_Rlwa4PKDI4R%7@Lgz21+$fr(4aK*aHGx3%w&csDA@f看一些精神上的東西,或者穿插跟別人之間的關係。

Camera, 2004
(圖/Shen Wei-《Self-portraits 2004》)
Q:你會如何形容《I Miss You Already》的身體?
那時候還年輕,有個健康、具柔韌度與線條的身體,很健美,和現在的身體很不一A@FclYmSU-)jvz#PK(_Xi#EC6ZLKrV=4N7Sy@Zp#ZE*zju)iQa樣。但是這個差異不是美學上的,而是精神上的,去接受它也好,表露它也好。
年輕時最不能接受身體上的變化,自己胖了,看到皺紋啊等等。但一旦接受了,也會發現它的美感,你就可以繼續前進了。我覺得接受Dg(y9)B(!@pp^KpZcC6h@Yg!MeUTRg2JgQa*z&fV(f@8f=4$GX並沒有很難,作為藝術家,你必須要對各種可能性都很開放,一旦它發生了,你就面對它。
我有張照片是站在那,泳褲脫到膝蓋,從下面拍上去。那張照片我每次看,就會覺得哇我當初的身體是這樣的。那張照片身體弧度與光影都很明顯。我沒有很羨慕當時的身材,只是當時的Vbh(+m=5tpDlcceooygU=caXWBX8PuS#Cw4VHaRrs@w(a1)ey^年輕,包括從肢體語言與身體表達出來的人生經歷。這張照片我覺得自己處於一個非常開放、放鬆、叛逆的狀態,但是現在我就無法自拍出那種感覺。
Q:如何拍出性感的自己?
我拍照時沒有太過考慮性感這個層面。我認為當你太過考慮性感時,你就在營造一種不是你自己的氣場。我覺得最自然的狀態最能表達一個人的氣場,我在拍照的時候一定要經過彼此交流達到舒服的狀態4_U1p8_76F1IWlOb!y!TUf3EfOzD9OY7!Nj4mB@EGb0OB@6b3o。性感是個主觀的東西,每個人對性感的批評都不同。越想要扮演一個角色,越無法把自己真實的一面表現出來。如果你想把自己拍成GQ上的模特兒,但你不是那樣的人,你拍不出那樣的氛圍。硬是要把自己放到模式裡面,我覺得不會成功。

Self-portrait (Fall), 2011
(圖/Shen Wei-《I Miss You Already》)
我覺得看自己的照片是最難的事情,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最會批評自己,同時也最不4r$huZ5E_BCmsr!yuya@wepUCt-aEDK-Ypm0shF1zLn&6TYe@b能接受自認為不好看的一面。但是如果你不去考慮這問題,你就不會有很大的壓力,要去追求「好看」。如果一個人太追求「好看」,那就是你無法接受這個事實。因為,如果你一旦接受自己的長相與氣場,自然而然就會可以找到能夠欣賞自己的人。不要刻意去融入大眾,就像我也聽到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我的自拍作品,這對藝術家來說是必然的。
我覺得框架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是性感的,但你不要把你的性感的那面,塞到那個框架中。在男同志圈有個陳規的形象(stereotype),不過它不是一個唯一的形象,不用特地融入。雖然很難,但是沒有別的方法。你不是凱文克勞的模特兒,你就不會變成那個樣子。這是個客觀的事情,所G)R90vE0xEU9cCnnwH4C$ZPcI@W7jH4uqfJr-KLKI^%3xj21)F以就接受它。

Self-portrait (Past), 2010
(圖/Shen Wei-《I Miss You Already》)
Q:你覺得透過藝術能夠促進同志平等嗎?
當然可以。美國的攝影師Nan Goldin,她在八零年代生活,當時的人們的性向很錯綜複雜,沒有明確的定義,同時八零年代也是美國陷入愛滋恐慌的時期。我接觸她作品時剛開始學習攝影,也剛到紐約,所以是透過她的作品了解這些歷史。如果藝術家沒有曝光相關的事物,如果Nan Golding不去曝光這些性的東西,那社會就沒有機會去了解這個層面的東西。很多藝術家的作品都會潛意識或有意識地去促進平等。它是用最直接視覺的感覺,潛移默化地帶動人7tAcI=YA*Gu%F8xMQ5i0-=H89_&nhY4h(0vWgI8dgo3W(k&K4l跟人之間的理解。
台灣目前尚未有機會能夠看到沈瑋的展覽,如果你喜歡沈瑋的作品,歡迎到他的網站上觀看更多非常棒的創作!